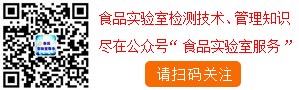格里非斯
發現DNA的遺傳功能,始于1928年格里非斯(P.Grif-fith)所做的用肺炎雙球菌感染小家鼠的實驗。
肺炎雙球菌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或品系。一個是有毒的光滑類型,簡稱為S型。一個是無毒的粗糙類型,簡稱為R型。S型的細胞由相當發達的莢膜(或稱為被囊)包裹著。莢膜由多糖構成,其作用是保護細菌不受被感染的動物的正常抵抗機制所殺死,從而使人或小家鼠致病(對人,它能導致肺炎;對小家鼠,則導致敗血癥)。但在加熱到致死程度后,該類型的細菌便失去致病能力。由于莢膜多糖的血清學特性不同、化學結構各異,S型又可分成許多不同的小類型,如SⅠ、SⅡ、SⅢ等。而R型細胞沒有合成莢膜的能力,所以不能使人或小家鼠致病。它不能合成莢膜的原因在于一個控制UDPG一脫氫酶的基因發生了突變,R,S兩型可以相互轉化。
1928年,格里菲斯將肺炎球菌SⅡ在特殊條件下進行離體培養,從中分離出R型。當他把這種R型的少量活細菌和大量已被殺死的SⅢ混合注射到小家鼠體內以后,出乎意外,小家鼠卻被致死了。剖檢發現,小家鼠的心血中有SⅢ細菌。
這一實驗結果可以有三種解釋。(1)SⅢ細菌可能并未完全殺死。但這種解釋不能成立,因為單獨注射經過處理的SⅢ時并不能致死小家鼠。(2)R型已轉變為S型。這一點也不能成立,因為剖檢發現的是SⅢ不是SⅡ,R型從SⅡ突變而來,理應轉化為 SⅡ。(3)R型從殺死的SⅢ獲得某種物質,導致類型轉化,從而恢復了原先因基因突變而喪失的合成莢膜的能力。格里菲斯肯定了這種解釋。這就是最早發現的轉化現象。
三年之后,研究者們發現,在有加熱殺死的S型細菌存在的條件下,體外培養R型的培養物,也可以產生這種轉化作用。此后不到兩年,又發現S型細菌的無細胞抽提物加到生長著的R型培養物上,也能產生R向S的轉休(R→S)。于是,研究者們提出,加熱殺死的S型細菌培養物或其無細胞抽提物中,一定存在著某種導致細菌類型發生轉化的物質。這種物質究竟是什么,人們尚不知道,為便于研究,暫時叫做“轉化因子”(transforming principle)。 格里菲斯發現轉化作用,為爾后認識到DNA是遺傳物質奠定了基礎。艾弗里和他的同事麥克勞德(C.M.Mcleod)和麥卡蒂(M.J.Mccarty)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才獲得了重大的突破。1944年,在紐約洛克菲勒研究所,艾弗里等人為了弄清轉化因子的化學本質,開始對含有R→S轉化因子的SⅢ型細菌的無細胞抽提物進行分餾、純化工作。他們根據染色體物質的絕大部分是蛋白質的事實,曾一度推斷蛋白質很可能是“轉化因子”。然而,當他們使用一系列的化學法和酶催化法,把各種蛋白質、類脂、多糖和核糖核酸從抽提物中去掉之后,卻發現抽提物的剩余物質仍然保持把R型轉化為S型的能力。于是,他們對自己的推斷動搖了。最后,在對抽提物進一步純化之后,他們發現,只消把取自SⅢ細胞抽提物的純化DNA,以低達六億分之一的劑量加在一個R型細胞的培養物中,仍然具有使R→SⅢ的轉化能力。他們還發現,從一個本身由R型轉化產生的S型細菌的培養物中提取的DNA也能使R→S。于是,他們得出結論說,“轉化因子”就是DNA。并在《實驗醫學雜志》第79卷第137期發表了這一研究成果。
艾弗里等人的試驗和結論是對脫氧核糖核酸認識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徹底改變了它在生物體內無足輕重的傳統觀念。艾弗里等人在1944年所作的試驗和結論,不僅沒有使科學界立即接受DNA是遺傳物質的正確觀念,反而引起了科學界許多人的極大驚訝和懷疑。當時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否定意見。第一種是,即使活性轉化因子就是DNA,也可能只是通過對莢膜的形成有直接的化學效應而發生的作用,不是由于它是遺傳信息的載體而起作用的。第二種否定意見則根本不承認DNA是遺傳物質,認為不論純化的 DNA從數據上看是如何的純凈,它仍然可能藏留著一絲有沾污性的蛋白質殘余,說不定這就是有活性的轉化因子。
科學界的懷疑、否定,不但沒有能動搖艾弗里等人繼續探索的堅定信心,反而加強了他們的信念,為進一步明確、探索而奮斗。
為了回答第一種懷疑論,泰勒(H.Taylor)和哈赤基斯(R.D.Hotchkiss)先后做了大量的實驗工作。特別是他們在1949年所進行的實驗,給了懷疑論者以致命一擊。泰勒從粗糙型(即R突變型)品系中分離出一個新的更加粗糙、更加不規則的突變型ER,并且發現從R品系細胞中提取出來的DNA可以完成ER向R的轉化。這樣,就證明了在以往實驗中作為受體的R品系本身還帶有一種轉化因子。這種轉化因子能把R品系仍然還具有的一點點殘余的合成莢膜的能力轉授給那個莢膜缺陷更甚的ER品系。不僅如此,泰勒還發現,將從S品系(作為給體)提取的NDA加到ER品系(作為受體)中,也能實現ER向R的轉化。如果把這種第一輪的R轉化物抽取一些加以培養,然后再加進S給體的DNA,便會出現R向S的轉化。泰勒的這些發現使得那些曾抱有“DNA僅僅是在多糖莢膜合成中作為一種外源化學介質進行干擾而導致轉化作用”這種信念的人們,無言以對,只得認輸。
在同一年內,哈赤基斯還證實了那些與莢膜形成毫無關系的一些細菌性狀(如對藥物的敏感性和抗性)也會發生轉化。他從正常的S型肺炎球菌中分離出了一種抗青霉素的突變型(記為PenrS),提取出它的DNA,加到一個由對青霉素敏感的S型中突變產生的R型(記為PenrR)的培養物中。結果發現,某些個Penr—R受體細菌已被轉化為Penr—S給體型。據此,他得出結論說,肺炎球菌的DNA不但帶有為莢膜形成所需要的信息,而且還帶有對青霉素產生抗性的細胞結構的形成所需要的信息。他還認為,莢膜的形成和對青霉素的抗性似乎是由不同的DNA分子控制著。此后不久,哈赤基斯又利用從S野生型抗鏈霉素突變型細胞中提取的DNA進行試驗,也獲得了同上述實驗完全相仿的結果。當哈赤基斯將其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發表之后,一切認為 DNA的轉化作用是生理性的而不是遺傳性的各種奇談怪論便消失無蹤了。
針對第二種否定意見,艾弗里和麥卡蒂于1946年用蛋白水解酶、核糖核酸酶和NDA酶分別處理肺炎球菌的細胞抽提物。結果表明,前兩種酶根本不影響抽提物的生物學效能,然而只消碰一碰后者,抽提物的轉化活性便立即被完全破壞掉。這一結果進一步證明了DNA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的功能。哈赤基斯繼續對轉化因子進行化學提純。到1949年時,他已經能把附著在活性DNA上的蛋白質含量降低到0.02%。盡管如此,在1949年,這些實驗結果仍然沒能使懷疑論者相信DNA是遺傳變化的原因所在。甚至到1950年,米爾斯基(A.E.Mirsky)仍對艾弗里的轉化因子試驗結論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很可能就是DNA而不是其它的東西是對轉化活性有責的,但還沒有得到證實。在活性因子的純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附著在DNA上的蛋白質被去掉了,……但很難消除這樣的可能性,即可能還有微量的蛋白質附著在DNA上,雖然無法通過所采用的各種檢驗法把它們偵察出來,……因此對DNA本身是否就是轉化介質還存在一些疑問”。
后來,隨著對DNA化學本性的足夠了解,特別是1952年赫爾希(A.D.Hers-hey)和蔡斯(M.Chase)證明了噬菌體DNA能攜帶母體病毒的遺傳信息到后代中去以后,科學界才終于接受了DNA是遺傳信息載體的理論。美國分子遺傳學家G.S.斯坦特寫道:“這項理論到1950年后好像突然出現在空中似的,到了1952年已被許多分子遺傳學家奉為信條”。
科學界對艾弗里等人的理論的懷疑,也反映到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中。當艾弗里提出他們的理論以后,閘有人提議艾弗里應獲這種最高獎勵。但鑒于科學界對其理論還抱有懷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認為推遲發獎更為合適。可是,當對他的成就的爭議平息、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準備授獎之時,他已經去世了。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只好惋惜地承認:“艾弗里于1944年關于DNA攜帶信息的發現代表了遺傳學領域中一個最重要的成就,他沒能得到諾貝爾獎金是很遺憾的”。
艾弗里等人的科學發現為什么遲遲得不到科學界的承認呢?這當然不是由于他們的不術地位低下所致,因為艾弗里那時已經是細菌學界的一員老將。不是由于出版機構的壓抑,因為他拉的文章在《實驗醫學雜志》上得到了及時發表。也不是由于他們的研究超越了時代或離開了研究的主流趨勢,因為當時有許多人都在研究格里菲斯發現的新現象。馬克思主義認為,艾弗里的發現的蒙難主要由于認識論方面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具體說來是:第一,傳統觀念的束縛。無庸否認,大家早就懷疑過DNA在遺傳過程中是否有一定的功能,特別是自從福爾根(F.Feulgen)于1924年證明了DNA是染色體的一個主要組分之后。但是,由于科學研究發展的特定歷史進程,人們對蛋白質的研究羅為充分,對它的重要性和分子結構的認識比較深入;而對DNA的研究就非常不夠,因而人們也就很難設想DNA能夠作為遺傳信息的載體。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仙,DNA不像蛋白質那樣引人注意。這除了它不像蛋白質(特別是酶)那樣到處都是,且到處都是活躍以外,重要的一點還在于結構上似乎沒有蛋白質那樣變化多端,具有個性(同一生物體中的異源蛋白質之間,或者不同生物體中的同源蛋白質之間,在結構的特異性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直到30年代后期,科學界還普遍堅持萊文(P.A.T.Levine)在20年代提出的“DNA結構的四核苷酸假說”,認為DNA只不過是一種含有腺苷酸、鳥苷酸、胸腺苷酸和胞苷酸四種殘基各一個的四核苷酸而已。到了40年代早期,盡管已經認識到DNA分子量實際上要比四核苷酸理論所要求的大得多,但是仍然普遍地相信四核苷乃是那較大的DN聚合體的基本重復單元,其中四個嘌呤和嘧啶堿基都依次按規定的序列而被重復著。DNA被看成如同淀粉等聚合物一樣的一種單調的均勻第二,錯誤地總結經驗造成的因噎廢食。
就在艾弗里等人做出上述結論的20年之間,著名生物學家、1915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威爾斯塔特在實驗中由于采用的酶溶液過于稀釋之故,以至用通常的化學檢驗法顯示不出它的蛋白質含量,但仍存在催化活性,于是便做出了酶不是蛋白質的錯誤結論,宣稱已經制成了不含蛋白質的酶的制備物。由于這種結論出自權威之口,人們信以為真,結果使對酶的研究推遲達10年之久。1944年時,科學界對這種前車之鑒仍記憶猶新。所以,當艾弗里等人公布他們的結論后,害怕再受騙的科學界便不敢再盲然唯這位權威而是從,遲遲不予認可了。播種苦果的是已故權威威爾斯塔特,而蒙受苦果之害的是在世權威艾弗里。殊途而同歸。“威爾斯塔特的錯誤幽靈使基因的研究又拖遲10年之久”。艾弗里等人及其科學發現的不幸遭遇,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首先,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們應當努力克服思想上的保守性和片面性,做到不為流行觀念所束縛,努力去揭示未曾為大多數人所注目的新領域;做到正確總結經驗教訓,不能因噎廢食。其次,作為一個科研管理工作者,我們不僅應對那些成果在短期內就得到證實的發現者給予獎勵,而且也應對那些其成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得到證實的卓越發現者(特別是其中的高齡科學家),及時給予承認。
 手機版
手機版